时间:2023-02-21 来源: 责任编辑:秘书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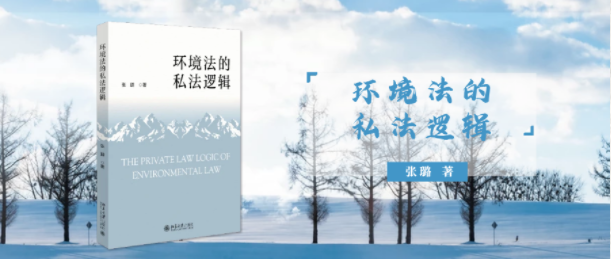
文章来源:《环境法的私法逻辑》,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张璐,法学博士,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环境法教研室主任。研究领域为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兼任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上海市法学会环境和资源法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崇明区委、区政府法律顾问。
《环境法的私法逻辑》目录
•方法与理念
环境法与生态化民法典的协同/003
环境法学的法学消减与增进/035
从利益限制到利益增进——环境资源法研究视角的转换/065
部门法研究范式对环境法的误读/078
•权利与义务
容忍义务的扩张与限缩——以容忍义务为参照的环境权理论批判与重塑/091
公民环境法律义务的法理与实践——以垃圾分类投放为研究样本/108
公众自测环境信息的法律分析——兼论环境知情权实现途径的完善/124
生态经济视野下的自然资源权利研究/138
《矿产资源法》修改中的“权证分开”问题研究/151
自然资源作为物权客体面临的困境与出路/161
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主要问题与应对思路/169
气候资源国家所有之辩/182
•损害与救济
环境司法专门化中的利益识别与利益衡量/195
中国环境司法专门化发展的功能定位与路径选择/217
自然资源损害的法学内涵解读——以损害与权利的逻辑关联为视角/237
论自然资源财产权利侵害的侵权责任——类型化的视角/249
“弃风弃光”环境公益诉讼案的法律理性审视/266
环境法中的公法逻辑惯性与成因
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实践中,环境法都被打上了明确的公法烙印,这一特征在环境法形成发展的整个过程中都有鲜明体现,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的环境法理论与实践,在这个问题上也基本上达成了共识。在中国环境法理论与实践的不同发展阶段,环境法中的公法逻辑都备受推崇。有学者指出,环境法是“运用公法手段调整私法领域的法部门”,也有学者的结论更为直接,断言“环境法应该视为公法无疑”。就环境法立法的实践来看,从1979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至今,中国的环境法立法始终采取“管理法”模式,有着较为明确的公法导向。虽然不同国家环境法形成的轨迹并不一致,但在公法因素对环境法的强势影响问题上,各国环境法的立场大致类似。以美国为例,许多主要的行政法案例其实都是环境案例,甚至只使用环境案例就可以进行一门行政法课程的教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的环境法是作为行政法的一个组成部分存在的。公法逻辑在环境法中的强势影响并非偶然,该局面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可大致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与立法者对环境问题的法律认知有关。无论从何种角度解读环境法的起源,环境问题都是其中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对环境问题的法律认知,决定了环境法形成的起点与基本走向。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明确的致害因素,与传统损害不同,环境问题所致损害表现出比较明显的扩散性、公共性特征,这决定了环境法从其形成伊始即定位于应对环境问题所致的公共性损害,实现环境公共利益保护的目标,“未来的环境法以及环境法学都应该以环境公共利益及其维护作为环境法以及环境法学的逻辑起点”。当公共利益成为环境法的基本范畴,相关理论研究必然条件反射般地将其与公法联系起来。回顾公法与私法划分的源头,“在古罗马人看来,他们之所以划分公法和私法,是因为他们认识到社会中存在两种利益形式,即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两种不同利益形式的存在决定了必然有调整私人利益关系的私法和维护公共利益的公法存在。”将公共利益作为公法形成的基础,在传统的法律观念中不证自明,环境法作为环境公共利益的法律表达,以公法逻辑的构建为基础也就顺理成章。
另一方面,受到法律在整体上演变的阶段性影响。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法律在整体上的发展演变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罗马法作为法律早期发展的主要代表,私法几乎占据了其全部空间而公法备受忽视,“在古罗马时期,凡是标明公法的内容几乎都不能引起罗马法学家们的兴趣,也没有获得他们向私法投入的那种强烈的情感……罗马法学也被称为罗马私法学。”
以古典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为依托,从罗马法开始,私法在法律的发展演变中一直占据主体地位,这种影响一直持续至20世纪初期。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后,古典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受到普遍质疑,“守夜人国家”开始向“行政国家”转变,以行政法为代表的公法也随之崛起并在法律体系中发挥出导向性的影响,在这个阶段,现代意义环境法出现的各种条件逐步具备。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公众日益关注人类健康和安全以及自然环境遭受的威胁,这同样促进了新的行政机关和新的规则的创立”,这些“新的行政机关和新的规则”是20世纪60年代环境法开始在美国等工业化国家逐步确立的机构和制度基础。环境法作为法律在整体演变过程中公法彰显导向影响阶段的产物,来自公法的先天影响难以摆脱,其后天发展也必然具有明显的惯性效应。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中国环境法的发展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末,从时代背景来看,当时的中国仍处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行政权占据优势地位,加之工业化国家环境法对行政因素倚重的示范性影响,“官”和“管”成了中国环境法的主旋律,命令加强制成为中国环境法实施的基本路径依赖,以公法逻辑为基础的制度构建也就理所当然。
环境法中私法逻辑的滋生与成长
环境法中的公法逻辑发展充分且影响强势,这是客观事实,然而需要追问的是,除了公法逻辑之外,私法逻辑在环境法中是否存在并有衍生可能?事实上,如果从环境法的形成过程来看,其私法基因尤其是民法的渊源是明确存在的。“环境问题的解决,是以民事救济为起点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早期的环境法理论大多集中于有关环境侵权救济的私法性分析上”,“在环境私法责任上只能根据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来确认,包括相邻权关系、因环境问题而引起的人身与财产侵权责任关系以及法定的容忍义务和违约责任。”虽然私法机制不能完整回应环境问题的公共性,但这并不意味着私法逻辑在环境法中完全没有存在必要和成长空间。实际上,在公法逻辑逐步彰显其主体地位的同时,环境法中的私法逻辑也在不断滋生和成长,体现在理论及实践两个维度。
环境法上的利益应涵盖社会个体基于环境而形成的利益诉求。“环境公共利益是环境利益的重要利益形态,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个体不能提出对环境生态利益的利益诉求”,事实上,“公共利益的维护,其背后体现了对环境、人权、社会正义和公民权利等方面的多重保护”,“环境公共利益具有普惠性和共享性,公共利益的最终归属主体是社会公众,每一个体都从公共利益中受益。因此,普惠性意味着,不可能将任何公民排除在环境公共利益的享受主体之外,每个公民都可能享受环境公共利益。”因此,社会个体对环境的利益诉求与环境公共利益的实现交织共存,环境公共利益的实现程度与个体环境利益诉求保障水平密切相关,对个体环境利益的保障以及在此基础上推进环境公共利益的实现,都是环境法应追求的目标,但为避免“公益裹挟私益”的情形,需要对两者进行明确区分,最高人民法院前副院长江必新曾指出:“要区分环境私益和环境公益,根据公益和私益的特点探寻有针对性的保护方式。”
由此可见,社会个体提出环境法上的利益诉求在理论上有充分的正当性,个体利益也应作为环境法上的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体利益具有鲜明的私益属性,这种基于私益而形成的权利诉求,无疑需要私法上权利的回应。环境法中私法权利的形成与确认,不仅是相应私法义务设定的重要前提,也为私法救济机制确立的正当性和必要性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预设要素支持,成为环境法中私法逻辑构建的基本起点。
近年来,环境司法专门化在中国的快速发展也为环境法中私法逻辑的成长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中国环境法在长期的发展历程中,法律实施的路径依赖非常单一,基本上以行政监管为主,但这种局面近年来发生了显著改变。2012年以来,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先后修改,中国于2015年确立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并形成迅猛发展势头。在环境公益诉讼的带动下,司法因素在环境法实施过程中的比重和影响迅速扩大,专门化的环境司法正在成为令人关注的司法领域。环境司法专门化在中国的兴起,不仅体现了环境法实施机制多样化的发展趋势,更为重要的是,其隐含了环境法中的私法逻辑。从行政和司法的基本功能侧重来看,“行政是以公共利益的实现为任务的作用,司法是以私人利益的保护为目的的作用”,司法与私益保护具有天然的内在关联。从表面上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确立是中国环境司法专门化的起点和重要象征,“从本质上说,环境公益诉讼中的诉权来源于公民对良好环境所拥有的基本权利”,其传达出了明确的私法逻辑信号。首先,将公益诉讼置于“民事”的前提下,体现了引入私法机制对环境公共利益保护的制度设计取向。其次,就目前已经作出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判决的内容来看,“侵权”成为援引法律条文以及判决说理的重要关键词,侵权概念本身天然带有浓厚的私法逻辑意味,将侵权作为支撑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判决的基本要素,无疑意味着当前环境司法专门化实践对私法逻辑的确认和贯彻。
环境法中私法逻辑推衍的基本面向
环境法中私法逻辑的滋生与成长,过往主要以潜在和隐含的表达为主,但就目前环境法的理论取向和制度环境而言,私法逻辑从“幕后”走向“台前”并发挥显性影响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如果将环境法中私法逻辑的构建作为一个明确的命题提出,首先需要确定其逻辑推衍的基本面向,以指引私法逻辑在环境法不同制度层面的落实。以一般意义上私法逻辑的展开过程为参照,并考虑环境法中私法逻辑成长点的需求,应将以下三个方面作为环境法中私法逻辑推衍的基本面向。
环境权的识别与确认。权利历来是私法的核心范畴,“我国制定民法典应突出权利本位”,权利无疑是私法逻辑推衍中的重中之重。长期以来,权利在环境法的理论与实践中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环境法中的基本权利在理论上阐释不清,在实践中湮没于公共利益及权力的光环之中。因此,如果将环境权作为环境法的基本权利,应将环境权的识别与确认作为环境法中私法逻辑推衍的首要问题。《民法典》人格权编中有关人格权和人格利益保护的一般规定为环境权的识别与确认提供了重要的规范依据,相关理论研究与制度设计的展开恰逢其时。
环境法中私法义务的辨析。义务是与权利对应的结构性存在,也是私法逻辑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在环境法的基础理论中,围绕义务的研究并不少见,但鲜有学者在私法逻辑框架内对义务进行理论阐释和制度设计。因此,在环境法私法逻辑推衍的进程中,需要基于私法的语境,阐明环境法中私法义务的形成背景与制度需求。《民法典》总则编中的绿色原则为民事法律行为设定环境保护义务作出了总括性规定,在物权编及合同编就环境保护义务的问题也相应作出了具体规定,这些规定为环境法中私法义务的辨析提供了结构性参照。
环境法中侵权责任的再定位。侵权制度既是环境法中最为传统的私法渊源,也一直是环境法与民法重叠与衔接的重点领域。《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专门设立“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责任”一章,是《民法典》生态化最为集中的制度设计。《民法典》的相关规定确定了环境侵权的基本制度框架,但从环境法的角度来说,环境侵权相较于一般侵权的特殊性何在,以及如何构建“权利—损害—救济”的环境侵权逻辑,都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这实际上涉及在环境法语境中对侵权责任的再定位,为《民法典》中有关环境侵权规定的落地提供充分的理论阐释和制度设计支持。
声明
本网站刊载的部分文字、图片、音频、视频以及网页版式设计等来源于网络。
原作者如不愿意在本网站刊登其内容,请及时通知本站,本站将予以删除。在此,特向原作者和机构致谢!
